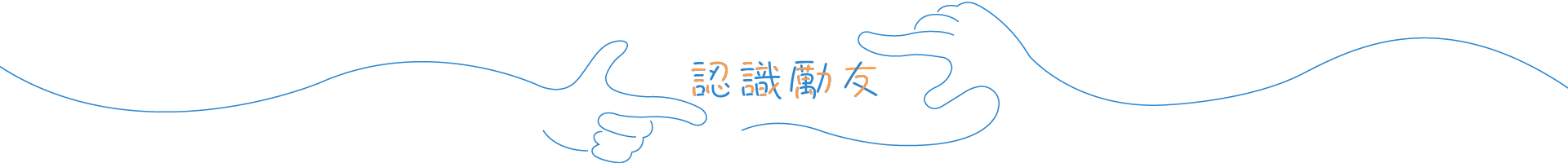文/中山大同區少年服務中心 少年 小阿飛
我的成長環境可能和多數人不一樣:父母在我3歲時離婚,各自重組家庭,新媽媽會和爸爸一起對我施暴。9歲時我受到性騷擾,向師長求助後得到「不要亂說話」的回應;讓我明白了任何事都只能靠自己,沒有人會幫助我。直到我遇見「社工」……
與社工的初遇,是在深夜的公園
第一次接觸「社工」,是在深夜的歸綏公園。面對突然靠近的「陌生大人們」,我們這群未成年都很緊張,擔心他們是不是來「找麻煩」。然而,自稱「社工」的大人卻和我們打成一片,還請我們吃肯德基;吃飽喝足後,我接過了一尾哥(社工)的名片。忘記過了多久,有次我被我爸揍的特別嚴重,不僅僅是身體上,讓我更難以承受的還有心靈上的虐待。面對家暴,我也習以為常了,只是這次在口袋摸到了社工的名片。抱持著「反正事情也不能再糟了」的想法,我打了名片上的電話……
那天,一尾哥帶我到一間教會的空房休息,但是天還沒亮我就跑了,因為我沒有安全感。我其實沒回家,而是輪流借宿在朋友家、便利商店、公園;也幾乎不去學校,因為老師說我惡劣的行為會影響同學,還規定我到校就得去「學務處」外面坐著直到放學。既然如此,我去幹嘛?
老師說會陪著我,然後我被上銬了
之後就我結識了一群「非主流」的年輕人,跟我一樣沒去學校,我就跟著他們遊蕩、飆車、打架、吸毒。某次回家,我被長輩栽贓,但礙於我過去的不良紀錄,沒人願意相信我。於是我帶著壓抑多年的情緒去理論,砸爛了家裡的東西,也把我爸打到掛急診。不久後,我被親人提起「刑事訴訟」,案由是傷害、毀損。我估計自己也是「凶多吉少」,就不打算去開庭。因為沒事做,我去了學校,輔導老師得知我要開庭,就主動承諾「他會陪著我去」,這讓我以為「我就會沒事了」。而事實是我剛坐下沒多久我就聽到「建議少年收容」,之後就被上銬了。
我不是一個人
等待進「少觀所」的十幾個小時,我不斷想要逃跑,直到我再次看到日初,我才認命。之後社工到「少觀所」看我,令我意外的是,他竟然相信我說的一切,即便我撒了些謊。少觀所收容結束後,我被迫住進「安置機構」,壓抑的環境、無法出門的種種限制,都讓我難以忍受。社工多次到安置住所找我聊天,關心我、鼓勵我、陪伴著我,讓我知道「我不是一個人」。在我最困難的時候,陪著我的不是家人,不是朋友,是這群「社工」。
之後我上了高中,再次受到導師的「區別對待」以及被針對,加上安置生活的束縛壓力,就在內心快要崩潰時,社工為我安排「諮商」,幫助我找到冷靜面對衝突的方法。之後又邀請我參加「樂團」,甚至偶爾能讓我「自行前往」團練,這種「被信任」的感受對我來說意義非凡。
在傷痕中長大的我
17歲那年,為了存學費我兼了三份打工,卻被拖欠薪水;社工得知後,主動陪我找老闆談。其實結果對我已不重要,重要的是——有人願意陪我面對困境,真心地在乎我!若不是社工當時接起了我的電話,若不是社工用一次又一次的「陪伴」,打破了我築起的防備,讓我感受到「被尊重、被肯定、被認同」,現在的我可能正蹲在哪個監獄。如今,我大學畢業了準備當兵,之後還想出國工作,給自己一個累積經驗的機會。我知道,我不孤單!
>> 中山大同區少年服務中心│青少年服務
>> 「定期定額」捐款支持「青少年服務」